“在这个世界,有一条供自己走的路。它通向何方?走就是。”
尼采早就知道这条路没有尽头,这条路的尽头也不会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在等候,所以他说“走就是”。至于该怎么走呢?走哪条路?我想尼采会说该走一条“超人”的路,一条创造“自我”的路。显而易见,福柯正是这条路上的探索者,而他的探索方式也恰是尼采所未实践的那种极限体验。
但在进行这种体验之前,首先做的准备工作就是忘掉“自我”,即抛掉被这个社会所建构出的身份。福柯从来不愿意被定位,对他而言这是一种主体性的丧失。就算只是说他是一位作者,他也会写一篇题为“作者是什么”的长文回应,作者什么都不是。除此之外,他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体验,也不愿把生活和写作挂钩。但米勒的这本自传,显然是把福柯的生活经历和著作结合在一起来阐述的。从上述的意义来说,这种阐述是否违背了福柯的想象呢?虽然福柯晚年对这种生活与作品两分的执念是有所松动,他知道谁都不能够逃脱生活去建构一个完全没有生活的学术领地,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会屈服呢?毕竟他一直走着一条反传统,反建构的路线。
当然抛开这个问题不谈,米勒阐述的福柯是精彩的,传奇的。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疯癫”“酷刑”S/M”的一系列讨论。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把病人关进疯人院,把罪犯锁进牢笼,把S/M理解为一种变态,似乎都是一种文明的想法,但福柯却以此为突破口,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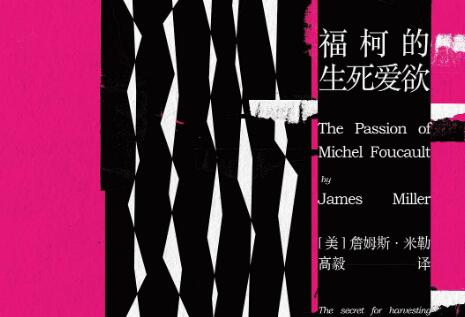
先说疯癫,疯癫在遥远的中世纪是作为一种审美的事实存在;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其曾有着启示真实的功能,而现代(从一种纯粹生物学角度)却被关进了疯人院。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文明的进步?是否意味着离真实更近一步?显然福柯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甚至直接解构掉“真实”这个概念本身。就如哥白尼之前地心说就是真实,只有哥白尼之后日心说才夺回阵地一般,真实本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其只是在人类发展史中不断被证伪的一个过程而已(当然最初是尼采提出的)。进一步,福柯认为人类对疯癫的态度也恰是如此,只是这一次恰是走了反方向而已。也就是说把疯人关进疯人院恰是一种最不文明的做法,其更多的隐藏了权力的实施。精神分析学家成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不正常倾向的权威,医生成了一种把疯癫纳入不道德之列的道德权威。这种无处不在权力被内化于社会的各个部分,成为了一种复杂的结构。这一部分在《规训和惩罚》之中体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也便是接下来要说的酷刑。
尼采和福柯也都提到酷刑其实是一种自我本能的外在化表现,其让权力关系变得异常明晰。比如最后被送上绞架的罪犯在面对公众的时候,可能会大声谩骂着教会、君主和体制,其将内心的压抑着的本能完全释放出来。虽然其最后被残酷的处以极刑,但这种君主从上而下的支配权却得以清晰的展现。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罪犯能够清晰意识到酷刑给予他的只有死亡别无其他,因此本能可以毫无顾忌的外在化,而公众也会意识到酷刑意味着对罪行的终极裁判,而这种绝对统治权来自于君主。与之相对的现代,罪犯被送进了监狱,在无休止的牢狱岁月之中,他们接受的更多来自于道德权威的审判,与酷刑相比,其本能被内在化了。也就是说,正是有着某种道德标准的存在,罪犯才会产生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比酷刑来得更让人难以接受。与此同时,权力关系也变得不再明晰,而是越来越精细和复杂化。比如监狱长可能会成为某个道德权威对罪犯进行无休止的劝诫,而罪犯似乎没有出路可言,只能无休止的认错。所以大体言之,以往的那种酷刑的惩罚机制消失了,内化于道德之中的更加严厉更加复杂的规训却产生了。这是一种人类本能的丧失,也是人文主义最大的“败笔”。
由此不禁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主人公),他同样怀着一套权力理论,即他清楚的意识到,拿破仑能够征服欧洲靠的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本事,像拿破仑一样成为一个征服者就可以摆脱自己跳蚤般的人生。他鼓起勇气拿起一把斧头,杀死了一个当铺行的老太婆,并拿走了她的钱包。他本以为能够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淡定自若,但事实却是他一直处在极度不安之中。这种不安不是来自于自我的良心谴责(因为他到最后都不承认他的理论是有问题的),而是来自周围人(不管是索菲亚,母亲和姐姐)的审判。这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审视,一种来自索菲亚的十字架中的“神圣力量”。与尼采一样,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质疑,和对非理性本质回归的渴望。
但问题又将出现,对非理性的追求就没有限度吗?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一命题最明晰的挑战(怪不得战后萨特也会提倡一种人道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也曾不止一次的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希特勒也成为了最典型的“尼采主义者”。但这终究是个难解的话题,所以福柯选择避开了这条路,转而走向了一种对身体快感的追求,即一种对肉体快感的极限体验。这是传记中将福柯自身的体验与其理论结合最紧密的一部分。福柯曾不断的去尝试新奇的体验,数次往返加利福尼亚的男同性恋俱乐部不说,作文www.yuananren.com还亲自体验了一把迷幻药。正如他所倡导的对快感的一种创新的追求不应该局限于性器官一样,他大胆的沉迷于这种“忘我”的体验之中。至于应该给予S/M一个怎样的定位,福柯似乎是将其理解为一种超验的快乐。也就是说受虐的状态是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痛苦。有点像弗洛伊德说的那种死亡本能一样,正是一种赋予其身的社会建构给予了自身太多的压力,让自我变得不再是自我。我们很难放下社会中的自我,转而去感受身体上的自我。而受虐恰恰是这样一种途径,即感受到被鞭打的痛苦撕裂的同时,也完全沉浸于痛苦的感受之中,这种感受恰是一种超验的快乐。
但是我们真的能从这种受虐中感受到快乐吗?还是说福柯另有其深意呢?其实S/M中还包含着一种更需要注意的关系,其游离于萨德所沉迷的那种肉体体验之外,这是一种受虐-施虐的关系。这与之前福柯所论述的“真实”相呼应,即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权力在不断重塑真实。如果我们以快乐作为真实的标准,那么作为一个施虐者会体会到支配的快乐;反之若是以痛苦为标准,会在一种被支配中体会到痛苦所带来的感官冲击。
显然福柯的这一些列极限体验在一般人眼中实属有些极端,但还是可以看到福柯一直在寻找这种“权力和知识”相互缠绕的螺旋式关系中的“真实”。当然这会招致很多批判,就如书中斯通所说的福柯“对控制、统治和惩罚的反复强调,将它们视作个人和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能的中介因素”一样,除了这种近乎形而上学般的建构以外,我们是否还需要用别的眼光去看看世界呢?是否还存在一条别的路去探寻福柯强调的那种“真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