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宿命式的走投无路:
华族出身的和子,美丽、率直。她读罗莎·卢森堡,她想要爱情和一场革命。可她真正能做什么呢?她不愿给皇族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因为那太丢身份。她也不愿意干农活,因为那太累。她真正轰轰烈烈做了的,是给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混蛋写了三封露骨,甚至作贱自己的情书。然后千里迢迢的把自己送上门,怀上那人的孩子。就此她有了“爱情”。她在革命前加上了“道德”,于是升华了行为,完成了革命……这,算不算读书人的意淫?
弟弟直治也是个读书人。他想革命,想改变自己的阶级,想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里。他想写小说,却没动过笔。他吸毒、买醉、玩女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向家里借钱……
还有“最后的贵族”,母亲。她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是因为她不仅能抬着头以最优雅的方式喝汤,还能反叛地,无视自己阶级地位地站着小便。可当家道中落时,她能做的也只是典当家产,对舅舅言听计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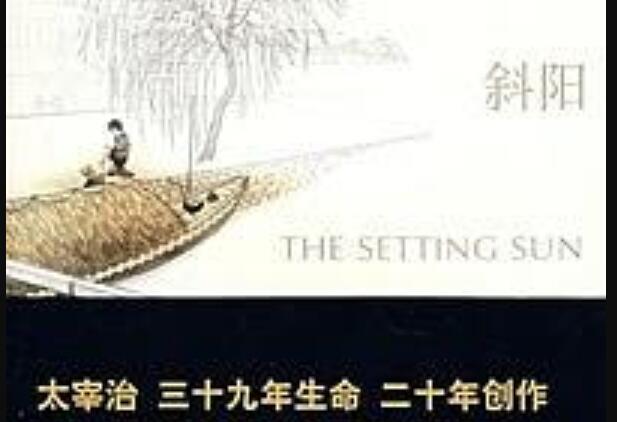
太宰治给书起名叫《斜阳》。是的,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斜阳早已不是正午轰轰烈烈的日头。它必将渐行渐下,无可挽留地沉入黑夜。
但使我忿懑于胸的,是这斜阳的悲剧并不单单只是时代的成因。与其说是贵族阶级的衰败,毋宁死说是这样一种概念的禁锢:生活不该是这样的呀!我有好的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比别人有更深刻的思想,我美丽、懂事又有趣。我难道不该有幸福的生活吗?抱歉。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思维怪圈里还没活过晌午就已跌入夜的深渊?
生活从来不是理应如何的,我们更多知道的是生活如何艰辛。即便有好的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只能说是占了一些优势。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影响着我们:健康、家人、社会的大环境…日本战败,家道中落,指望着像以前一样岁月静好是不可能的。理性面对现实,才是对自己,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去教书也好,去干农活也好,作文www.yuananren.com总比变卖家产要更实在。一家子靠卖家产能支持多久呢?家产卖光以后又要靠什么活着呢?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没有人想过。所谓理想主义文艺青年的眼高手低就是如此吧。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不如去做图书管理员。对自己的寄望过高,又不能脚踏实地做事,他们的死也许就是注定的命运。
还有一个不能不想到的问题,就是东亚国家个体的被动,特别是女性的被动。在面对变故的时候,我们习惯于社会(华族地位,咳,可惜贵族没落了)或权威(比如舅舅,比如无路可走时投奔那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情人”)为我们负担起责任。从没有一刻想起我们也可以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举个例子,同时代比她们大二十多岁的丹麦贵族凯伦·布里克森(《走出非洲》几乎是她的自传体小说),也同样一生坎坷,但每遇变故她都可以冷静地分析,为自己将来的生活做出合理的规划。丈夫常年不在,偶尔回来还给自己染上梅毒。
同样二十几岁的年纪,凯伦难道不慌张吗?但她可以冷静地分析,离开丈夫,先回欧洲治疗(这应该是她当初最好的选择)。她再一次回到非洲,客观地说是因为她的嫁妆几乎全部投进非洲的农场。她敢于直面问题,解决经济来源。她有所有文艺青年的特质,她也更喜欢在壁炉前讲故事,高谈阔论;喜欢精致的餐点;喜欢黑胶盘。但她也肯快乐地下地干农活、开拖拉机,扛死尸……因为这是该做的,她没有自怨自哀。我们不能说凯伦很精明,因为她虽然肯干,但咖啡园的投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何况之后又赶上了蝗灾(电影里是火灾)。所有积蓄毁于一旦,凯伦任然可以独立地冷静分析现状:及时止损,回欧洲发展。虽然在非洲,有一个她很爱的男人,但她没有一刻想过为他留下来。因为她知道,那终是靠不住的过眼云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