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喜欢把中国秦汉至唐代的历史称为中古,或者中世纪。这种分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汉魏以来长期存在的贵族门阀阶级不见了,在封建君主打压、割据战争和农民起义的联合作用下消灭殆尽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布变得扁平化。之后元明清基本没什么大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唐代是一个大转折时期。
与社会形态的转变相呼应的,是中国文学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最突出的就是诗歌的转变。清代诗论家冯班说:“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钝吟杂录》卷七)叶燮进一步断言,中唐不仅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
中唐,一般指的是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共70年时间,其间共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个皇帝。唐诗在这70年中的发展,又有几个代表性的发展三个阶段,一是(代宗)大历时期、二是(宪宗)元和时期,三是(穆宗)长庆时期。长庆时期仅有四年,风格不太明显,可以与元和时期并为一谈。
大历时期的诗人以活跃在朝廷的“大历十才子”和在地方为官的刘长卿、韦应物为首,还包括一些方外诗人,如皎然、灵一等,不过他们的整体水平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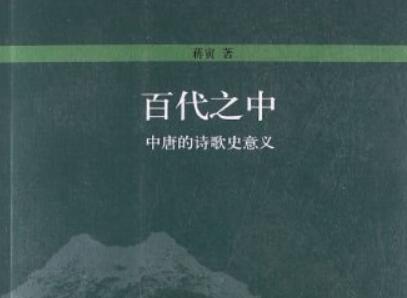
“大历十才子”的官位都不太高,但都有良好的艺术修养,擅长近体诗的写作,风格清空闲雅,韵律和谐流利,在技巧上颇为成熟。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钱起、卢纶、韩翃、李端、郎士元。他们最擅长的题材是践行送别。当时钱起、郎士元的送别诗很流行,成为一种时尚,《中兴间气集》里记载:“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践,诗论鄙之。”
刘长卿和韦应物是大历时期少有的能在诗歌史上独成一派的名家。刘长卿仅比杜甫小14岁,天宝年间就已经中了进士,安史之乱爆发时,他大约29岁。然而他的诗毫无盛唐之风,胡应麟说他“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诗薮》内编卷五)。他的诗大多凄冷悲凉,或许与他的性格有关系。
韦应物最为人推崇的还是五言作品,白居易称其“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他在人格和艺术理想上倾慕陶渊明,诗歌技巧上则吸收谢灵运、谢朓的优点,形成气貌晴朗温润、意境淡远超诣,语言洗练自然,节奏舒缓不迫的风格特点。
整体而言大历诗是盛唐诗向中唐诗转变的过渡阶段,它既是盛唐诗的延续,又是中唐的先声。大历诗人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口号,所以人们不太容易把握他们的创作特征。但是,只要比较《河岳英灵集》(753年)和《中兴间气集》(779年)就可以发现,短短二十几年,唐诗不动声色地完成了由盛唐到中唐的过渡。对社会生活的态度由浪漫变得现实,对诗歌的趣味“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胡震亨《唐音癸签》),对诗体的好尚由古体转向近体,题材选择由表达理想、感性咏怀转向日常生活、身边琐事。
元和时代是唐诗的第二个高潮,前人所说的“中唐”,一般指的就是元和时代。唐诗经过大历时代的低迷和酝酿,唐诗到元和时代再度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这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代表人物有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刘禹锡等人。
在近体诗日益走向成熟,尤其是在大历诗专工近体,古诗写作严重律化的情况下,元和诗人重张盛唐的古诗和乐府传统,以庞大的体制和冗长的诗题来强化诗歌的纪实性和叙事性,用取才的无所不包、表达的反常变异、声律的避熟用生来开拓新奇的诗境,用写作日常化、语言口语化、形式游戏化的实验写作来反抗陈腐的诗歌经验,一扫大历诗的陈意、陈调、陈体,达到“惟陈言之务去”的目的。这些变革凝聚着一股探求诗体潜能和语言张力的动力,引导着元和时代总体上颠覆传统感觉秩序,脱逸古典诗歌规范,破坏古典美学趣味的强烈倾向——举凡均衡、对称、和谐、典雅、有据等艺术原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诗歌的古典审美理想中开始渗透进不和谐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和诗可以说是“百代之中”,成为划分中国古代诗歌史前后两大阶段的分水岭。
本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除第一篇是概述大历到元和诗风的变化情况外,其他几篇文章都是分关于个人的专题论述,分别讲了孟郊、权德與、贾岛、姚合、李贺、韩愈六位诗人。其中对权德與的叙述略多了一些,用了三章的笔墨,其次是韩愈,用了两章笔墨。之所以如此安排,并非是作者觉得权德與诗写得很好,而是因为作者觉得权德與作为当时的文坛主盟,其对诗人们的影响比较大,而这一点在过去被众多研究者忽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章中,作者专门讨论了权德與的赠内诗。通过作者的梳理我们发现,在唐人的赠内诗中,权德與写得最多,而且最真实。所谓真实,指的是诗人真的是把妻子当做读者来写作的。作者拿权德與和李白相比,作文www.yuananren.com所李白的赠内诗,在写个妻子的同时,也是写个世人的,从诗题的“赠内”、“寄内”就表明,它不是夫妻间的对话,而是诗人自己的“独白”。而权德與的赠内诗题目则是“有寄”、“有怀”、“寄赠”等,这是对话交流的诗题形式。也就是说,权德與不仅将妻子当作关心、描写的对象,更将她当作作品奉献的对象,在对等的关系上表达了对妻子的眷恋和爱情。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而可贵的,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中唐诗人众多,作者却没有将他们一网打尽,读者比较熟悉的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作者则完全没提。这对于那些想通过此书了解中唐诗歌全貌的一般读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对于那些对中唐诗歌相对熟悉的读者来说,作者在挖掘中唐诗歌流变的细节方面,则委实有许多新发现,读来一定会觉得耳目一新。郑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