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在给《时间的女儿》写的导读里,借朋友之口说过一句名言——“我这辈子所知道的最好的推理小说是,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
然而本书当然并非推理小说,而是有关方以智晚节的数篇论文合集。考证当然会运用到推理,但考证显然不止是推理。本书除了运用以“实证方法”为主体的传统考证方法外,还运用了“诠释方法”,因为“本书所考者,则古人之心也”,而“言为心声”——“苟善解古人之言,则古人之心亦未尝不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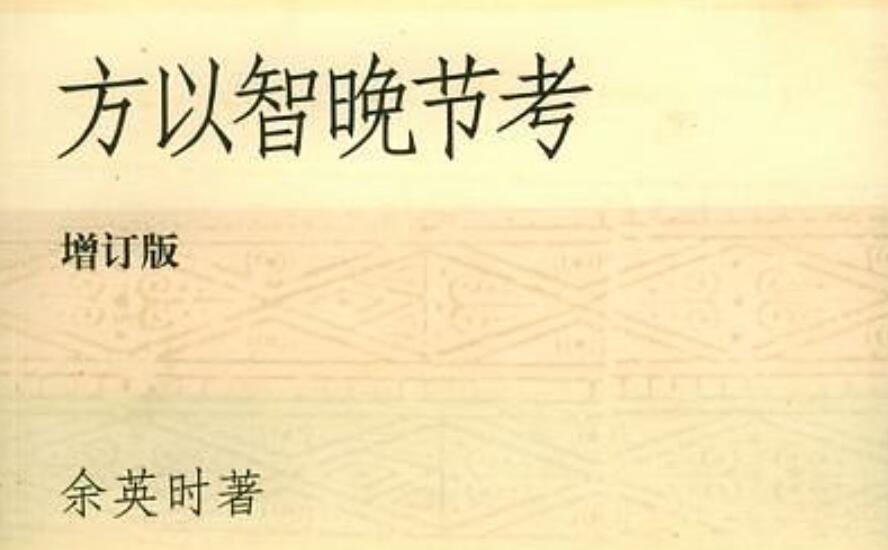
明清易代,天崩地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痛史。前人多有著述,如陈寅恪之《柳如是别传》,实借彰表遗民之志节而抒心中之幽愤。《方》书亦如是,以方以智在明亡后的行踪与交游为线索,考稽各家诗文、杂史、方志、碑碣等,钩沉索隐,期以发扬遗民士大夫的“潜德幽光”。钱穆先生称许“三百年间一若沉若浮若隐若显之人物,乃得跃然如在纸上,宛然如在目前。”
《方》书对方以智晚年行踪、交游之考证详密且相当精彩,但最最紧要的“死节”,似乎依然颇成问题。在方以智究竟是病死还是自沉这个问题上,无疑只有一个真相。但是余英时先生引证的诗文,实不足以定谳这一“罗生门”。再者,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称方以智参与复明活动的“证据不免薄弱”,这点余英时先生在书中亦自云“以待他日之论定”。若无涉复明之事而明亡后二十七年方“死节”,未免说不过去。余英时先生的方法当然并无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文献不足。导致方氏父子罹祸的“粤案”目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材料,此案的内情不清,方以智作为遗民的晚节虽无可訾议,但临终是否作为志士“死节”似乎还不能盖棺论定。虽有“同情之理解”,但依旧希望更有后来者“拿证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