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冲击非常大,先谈一点大概,日后慢慢讲。)
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奇幻)小说家,爱尔兰的洛德·邓萨尼。据说他曾深远影响了H.P.洛夫克拉夫特(还有托尔金,但这人排不上号,不提)——最近读过好几个影响了H.P.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家,但这位邓萨尼勋爵在我看来十分接近卡夫卡的水平,他能把一个和卡夫卡头脑中相似的观念发挥到极致,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寥寥无几。
这些观念并非出自一个个隐喻,它们都是对史无前例的内心事件的描述,是一种在相对凝固的世界中构成为“自我”的方式,确实和“发明一种新的卡巴拉”这种举动(尽管大抵还不能这么说)在同一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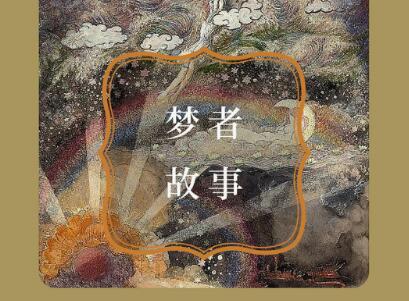
卡夫卡的“猎人格拉库斯”虽然死去了,但由于下冥府时走错了方向,所以仍然乘船在世界各地漫游,而出自邓萨尼的《梦者故事》的《浪淘墓》的主人公死去时发现自己无法被任何形式的葬礼埋葬,无论是土葬还是海葬,没有任何物质、任何地狱可以收容他,他被丢弃在河边的泥沼中,也曾被狂风卷到群岛,但总是回到同一地点,面对一排死屋。
令猎人格拉库斯感到窒息的是他写的东西无人能够看到,而无法下葬的伦敦人受到的诅咒则是无法哭泣。《浪淘墓》的结局又像是卡夫卡的《十一个儿子》在结局时出现的狂想:被鸟带走——被不认识人类的群鸟欢唱着带往天堂。
《在法的门前》,进城者需要向守门人行贿,即便如此也没有成功;邓萨尼的《妄城记》则开篇提出了法律是什么,尽管这个法律看起来简单,它就是“这座城市有一个惯例,每一个进城的人都得交付一笔税款——在城门讲述虚妄的故事。”所以邓萨尼的短篇小说之间看起来也是有联系的,似乎是一个松散的体系。
因为《妄城记》中进城的法则,就是《浪淘墓》和《猎人格拉库斯》中的主人公在人们想读到自己写的东西、看到自己的眼泪,即世人回头想进入他们的“城市”时,所面临的要求。只有能讲出和主人公的经历同样虚妄的故事,他们才有进城的资格。除此之外,他们永远不能知道法律,不知道法律存在于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