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书》通过塞壬之歌与奥德修斯为引子进入对叙事的讨论——闪耀出叙事与叙事过程相遇的空间。普鲁斯特将真实生活与这一空间交叠——“在我身上再创了一个逾越了时间秩序的人。”逾越:就是将相似的真实事件交错地呈现,废除时间在各个事件中的关联,也因此肯定了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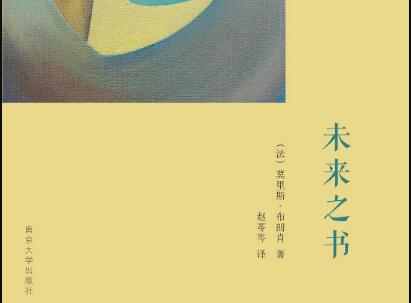
在回忆中,在经历之中,尤其是在各个不相关联的事件里,时间的起始点在哪?它的终点又在哪?在写作中,叙事事件的起始点即作为时间的起始点,当事件被记起的同时,写作时间的起始点得以确立,它独立于正经历着的分秒。交叠:在写作的分秒里,多个被废除与时间关联的事件同时出现,多个起始点出现在现时,让“现在”得以展开。写作的时间得以确立。
我们习惯把一个生灵的出生当作他关于现世的起始点。因为我们没有关于“世界”的回忆,无法确立“世界”的起始点,而出生仿佛就是一个刚被记起的事件,它割裂了真实的时间。对“世界”的回忆全赖于我们时好时坏的记事能力(这方面的时好时坏也延伸到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在“世界”扮演的角色要比想象中微弱。
“世界”即是文学的空间,某一生灵的降生意味着某一事件被记起;当生灵死去,事件依然在它的纬度中发展新的可能性,我们在写作的时间中与死去的生灵相遇,邂逅,进而产生新的叙事,死者的气质在活人身上显现,这便是文学所带来的可能性:在错与恶的空间保存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