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是发自内心的。至于死猫——故意杀害猫,理所当然地杀害它们——我碰巧遇到过很多次。在童年里,我会碰巧遇到这种事。那时候,猫是有害动物,起破坏作用,类似女巫,跟左手、倒霉运、女性气质一样——但从来没有人站出来攻击女性气质,除了一些人在喝得酩酊大醉时会跟另一些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讲起——如果后来某个倒霉的女性遇到了暴力——事后会归罪于伟大事业。男人和男孩杀害猫,就算没杀害,至少也会在路过的时候踢它们,或者用弹弓朝它们弹石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你碰巧遇到一只死猫,你不会特意提起。
日常伤害被日常接受,虐猫和杀猫彼此作用、互相补充。因为伤害太过普遍,人们失去了基本的感受能力,被暴力和伤害重塑,合理化麻木,从漠视到认同,一切都成了应当固守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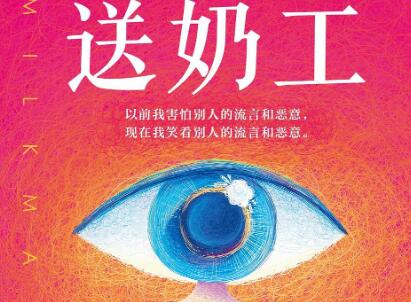
这又对应了法国18世纪发生的著名的“屠猫狂欢”。屠猫发生在当时的印刷工人之中,除了贵族,当时的人们普遍生活在“生活在一个举目皆是后母与孤儿、天地不仁、劳力无止尽、感情生活之粗糙与压抑令人不忍卒睹的世界”。(见达恩顿《屠猫狂欢》,新星2018年版)屠猫更像是一种“底层互害”的极端表现,这个世界如此不公,人们需要狂欢的仪式来发泄对那种固定秩序的屈辱和不满。小说中虐猫屠猫并非短时间内仪式性的狂欢,而是融入到生活之中随处可见,见怪不怪。从前总是和女巫联系在一起的猫隐喻着危险与情欲,这层隐喻和猎巫的"正义"消融在生活里成为传统。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且有生理呕吐反应的是高密度的流言蜚语。流言把子虚乌有变成了坚硬的依据,小说主角从受害者变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当内外骚动合而为一,语言暴力与肢体暴力汇流成一股令人窒息的风暴,席卷了个体的命运。后殖民主义研究巨擘斯皮瓦克说过,“流言能够激发一种认同感,因为它属于每一个‘读者’和‘传播者’,却无人是它的起源和渠道。”而这在一个具有浓厚殖民色彩并试图反抗的社会中如此明显,因为封锁而变得封闭,因为封闭而传统,因为反抗而自我固化——当流言与男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无所不在的压迫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种压迫对于“社区团结”“民族认同”甚至是必要的,另一层隐藏的意味是: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敌人尊重个体,保护弱者,我们偏偏不。极端环境下的社会心态和文化因素构成一个闭环,对于女性以及一切弱者和反叛者的伤害并非来自敌人,作文www.yuananren.com但和敌人密切相关,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自发的、模糊的、压抑的甚至扭曲的意识、心态和“文化传统”构筑了自我保护的高墙,高墙的材料里也充满了歧视、暴力和恶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