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条理清晰的句子解读一段梦呓,只能将梦和现实完全割裂开。
度过生活充实又条分缕析的白日,我已经许久不再做梦了,与生活相比,真是太久了。久到语言可以自己添加上前后因果,连接成段,把词语和词语之间的空隙,全部填满。
可是,语言、时间、位置、回忆、意识、梦。和标点。原本是断续又模糊的吧,是山泉砸在岩石峭壁上,打碎成几点一闪不见的星光,漂在空中;水流本身被木石堵死,间或蹦出一两滴水珠,接住散开的浮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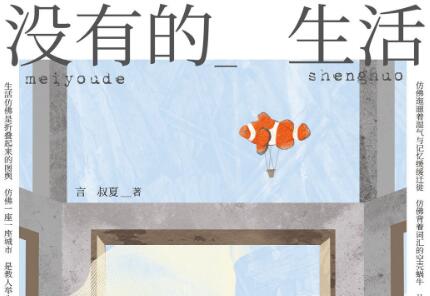
文字捕捉到文字。不依靠逻辑的锁链,只展示出这道空隙。是时间的,或是回忆的,或是梦的。穿插进生活里,当下的时刻也被割开,割成一个个时间片段。生活和文字共同潜入裂缝,在实实在在的事情之间,在白日的生活之中,造出一个夜晚,不真实的夜晚,属于任何年代,任何位置的,由梦境造出的,夜晚。海市蜃楼一般,才属于“没有的生活”。
属于台湾的文字,游荡在高雄、台北、花莲,在教室、宿舍、地下室缓慢发酵,理应象征着活力的地方,却透出一股阴冷的气息。回忆在距离搭建出的冰窖冷藏了太久,骨血冻在一起,看不出原本的形状。影院、小楼、电影的幕布,只剩下一块块剪影,拼接起来,粘出轮廓。无法拼合的缝隙,由梦呓填满,再转成文字。我们与台湾离得太远,与一幢幢小楼相距更远。幸好还有九〇年代、一〇年代,文字中回忆的时间会比地点更加能引发共鸣。
经历千禧年的文字,没有可以想见的跨进新世纪的狂喜,可惜我也没经历过那种狂喜。记录里一贯是平静的,平静得有点忧虑。也可能就是忧虑。和其他文字一样,没有什么明快的色彩,甚至有点郁结于心。是站在历史车头回望,看着幕布碾碎成一个个数字化的编码,发现落在上世纪的自己,慢吞吞不知所措,的一点忧郁。
“寻找着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花上一整个冬日去凝练一个喜欢的词”“别在猫面前换衣服”“地板必须有猫长年横躺瘫痪”“冬天应该是一只很渴的动物”……
文字浮现,随即消失。一篇文章中零星两三个词语,在唇齿间反复跳跃,炼成一个,再从尾音开始溶解,一点点滴回,两个标点之间。溜回去。分不清是我不想记住,还是文字不想让我顺着逻辑的链条,把它们一个个拎出来。作文www.yuananren.com便把这根链条,劈成数段,一截截挖出来,再埋进去,埋得更深。初见尚能记住题目,看罢竟连标题,都只记得一个轮廓,边缘虚化,连着背景的一团底色,色彩却似乎更清晰些。
像是,我记得做了一个梦,却连梦里出现的人、出现的时间、出现的地方,一并留在了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