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如此的扭曲。扭曲到让我觉得整本书的前半段几乎称得上一个女生的苦难史,从出生到青年时期,一个女孩最无助,最容易将自我价值观塑成,也最容易留下童年阴影的那几年,她的生活如同一只活在地窖下的老鼠,终日惶惶不安。
其实用惶惶不安来形容主人公塔拉的少年时期并不准确,因为只有当两种价值观相撞的时候,才会产生出不安与怀疑的情绪,但是在那段日子里,只有一种价值观得以塑造她,那就是父亲的权威。
作者以自序前半生的方式写下了这本“回忆录”,讲述了自己从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山区到17岁通过自考考上大学,最终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的历程,让人诧异的是,在17岁前她从未上过学。而在走出大山上学的期间,她和家人日渐深厚的矛盾,越走越远的距离与在冲破自我和完善自我人格之间得到相互贯彻,最终找到自己的天赋与力量。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学著作,它适合的群体属于那些在原生家庭里迷茫不安的孩子,属于那些被伤害被贬低被他人低估的孩子,属于那些想真正找到自己力量的孩子。而这样的孩子,女生居多,她们从小被教导顺从才是对家庭的忠诚,但是却没有人问他们是否知道———无条件的对家庭的顺从正代表着在另一个方面去弱化自己的人格?他们在压抑中成长,直到看到另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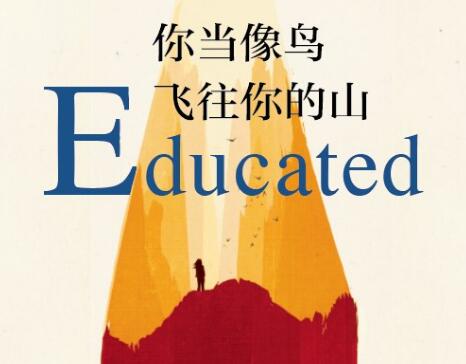
约翰·斯图亚特曾对探讨女性的力量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主题。“他声称:“许多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被哄骗,劝诱,推搡和挤压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赋和报复。”
塔拉出生在一个格外畸形的家里,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她并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甚至在她的童年里去顺从的配合这种畸形。
她的家庭中有几个孩子没有出生证明,根本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父亲以废料场为生,母亲则被父亲要求去学习当一个没有资格证的助产士与药剂师,因为这样他们的子子孙孙就都可以在家里接生,他们宁死也不去医院,母亲认为:“药物是有毒的,而这种毒,无论过了多久还会继续残留在身体里。“
父亲则患有躁郁症与被迫害妄想症,但他的父亲认为疾病也没什么大不了,而这种心态不是出于认为自己能战胜病苦的信念,而是出于一种无知,父亲认为疾病是上帝的赏赐,而人不应该违背上帝的意愿,所以他们从来不去医院,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去。
除此之外他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他认为学校是给人洗脑的场所,是政府的阴谋,是一种把自己的孩子从自己身边夺走的计谋。
这种话语熟悉么?很少有家庭像塔拉的家庭这样充满无知,但是却有很多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脱离自己的掌控,他们拒绝自己的孩子除了顺从自己的想法以外,有其他的想法。其他的想法在他们的眼中有许多的别称:幼稚,好高骛远,异类,还有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不适合你。”那么什么才是适合这8个孩子的呢?
在她父亲眼里是在家里的废料场里工作,是和危险的机械共舞,是永远留在大山里,是坐车的时候从来不寄安全带——因为生死,全都是依靠上帝的旨意。这无知如死海般寂静,家里的8个孩子都逐渐被淹没,没人愿意打破这片沉寂,直至被淹没,也没人发出求救的呼喊。
没什么能打破无知的僵局,除了教育,而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就是《educated》,直至最后,8个孩子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我们家人从中间一分两半——三个离开了大山,四个留了下来。三个获得博士学位,四个没有高中文凭。裂痕已经出现,而且越来越深。“
变化产生的原因正是有人在漆黑的无知里得以窥见”教育“一星半点的天光。最初是哥哥泰勒,他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紧张,口吃,他唯一的朋友是唱片与书籍,而这两样是他生命中爱与美的慈悲。
渐渐的塔拉也常常躲在他身边感受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泰勒是家人中最温顺的一个,但也是最先冲出去的那个,他选择飞出大山去上学,也认为妹妹塔拉应该参加自学考试。
就这样塔拉从17岁以前从未接受过教育,到自学考试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她的教育才打开了一个豁口。
渐渐的这个豁口被知识填充,被拉扯的越来越大,塔拉开始感到自我怀疑,她在大学里所感知到的世界与她16年前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16岁的时候她被家里的所有男性教育,穿裙子就是荡妇,她另一个哥哥肖恩每天都叫她“妓女。”她的哥哥会把她的头摁进马桶里,会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按到墙上,而当她日后在回忆起这些时,作文www.yuananren.com她的母亲只会告诉她——是你的记忆出错了,你哥哥没有问题。母亲的软弱,哥哥的暴力倾向,教授的仁慈,让塔拉在上大学的那段日子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折磨,暴力与救赎在塔拉的世界里不断崩塌与上演。
当塔拉获得去剑桥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她却深深的感到自卑,认为自己不配在这样闪闪发光的地方学习,他同学的父母是出色的教育家,外交官,但是自己的父亲却是半个疯子,而她的母亲在父亲面前已经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被顺从困住了手脚。
她的教授和她说:”你从没有想过,你可能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待着这里。“我更喜欢给别人上菜,”“塔拉说,”而不是吃菜。“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塔拉说,“一切都闪闪发光。”“你千万别这么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只有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什么样,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你自己。”
很多人说这本书的评分太高了,比尔盖茨的评语里也充满了惹人注目的噱头,可是拿到手来却发现这本书从塔拉上大学到青云直上变成哈佛的访问学者的过程中,并没有着重描写自己是如何彻头彻尾通过学习被教育改变的。是的,她并不是美国梦的化身,也不是美好的化身,《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从头到位讲的都是一个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她在30岁取得的成就是在无数次自我怀疑中堆砌而成的。
“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在她的青年时期,她的父母让她被苦难与无知包裹,而她却像鸟一样在教育这所大山中,找到了另一片的栖息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