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伊恩•莫里斯的《战争》,再读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有种脑力激荡、思想对冲的感觉。前者为国家张目,后者为游民撑腰。
前者认为,从长时段来看,暴力、征服、国家控制是一剂苦口的良药,它是所有坏的选项中最不坏的那种,它以短时段内屠戮、奴役和压迫一小部分人为代价,给长时段里的大多数人提供了安全、富足和繁荣。这一自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来,以“建设性的战争”为手段,在一万五千年的历史里不断整合社会的进程,使得人类从几百万繁衍出至今七十亿之巨的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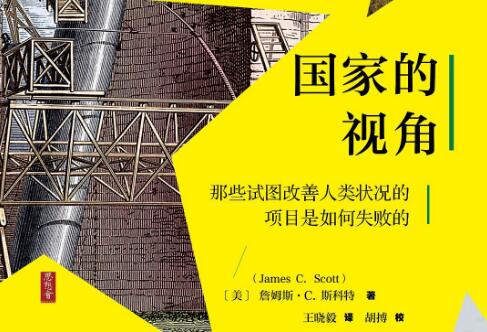
后者认为,国家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它总是以简单化、清晰化为目标,试图对其疆域内所有的人,以横平竖直的方式进行单一化的管理。能被框进国家行政税收体系中的即是良民,框不进来的就是刁民。能在国家单一化框架里应用的知识即是有用的知识。其余的地方性知识则是无用的知识,甚至成为知识应用中需要清除的障碍。要命的是,这种自负往往造成文化上的、生态上的和政治上的灾难。两种看待国家截然相反的视角,固然有其思想的脉络。
前者像是霍布斯,大讲利维坦之前的人类有多混乱,利维坦的降临带来了多少福音。后者像是卢梭,对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充满了憧憬,而对带上了社会枷锁的人性报以悲叹。
我倒是觉得,这种学术视角上的差异,可能跟学科背景及其连带而来的个人经历也有很深的渊源。莫里斯作为考古学家,田野里的常态是跟死人打交道,刨坑、寻骨、找器物。见过太多已经逝去千年万年的东西,看到的多是宏观的历史演进,不易体会到研究对象的切肤之痛。
斯科特作为人类学家,田野里的常态是跟活人打交道,聊天、唠嗑、拉家常。学到太多日常生活中有用的小事,听过太多被排斥、被歧视、被驱逐的故事,更易形成对研究对象同情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