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意识到读书的时候必须控制自己作为读者的感情的呢?大概是第一次看毛姆的小说时,情感被作者牢牢地攥在手中,什么时候被无情的捏碎,什么时候又被给予温柔的触碰。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擅于调教不同品种的宠物,而我彼时彼刻就像是作家调教过后,跟在他身后留着哈喇子的宠物狗。当我第一次思考:为何我不能客观的、不带有情感的去旁观他笔下的世界和人物呢,于是在今后的读书时我都会刻意地去将快要深陷于剧情的自己匆忙又决绝地拉回来。直到读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无语!’这便是我读完整本书之后最深切的感受。我倒不是将自己的形象与费尔明娜重合,而是以第三角色站在医生的身边,我是如此偏爱乌尔比诺啊!如此熟悉的偏爱,曾经在阅读毛姆的《面纱》时也对瓦尔特有类似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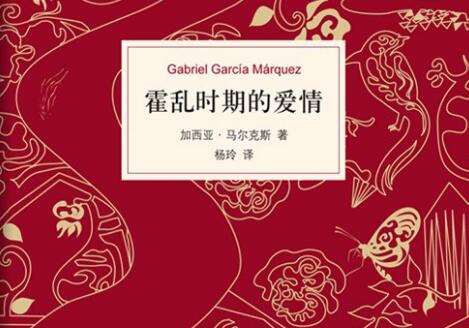
就在这时,骚动的人群分作两边,一辆被几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着的四轮马车驶了过来。哄笑停止了,不怀好意的人群散开去。伊尔德布兰达肯定永远也忘不了她第一次看见那个站在马车踏板上的男人时的情景:他那高高的缎子礼帽,他的锦缎背心,他的文质彬彬和他双眸的柔情,还有他出现时的威严。
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她再也受不了脚下那双靴子的折磨了。
“这再简单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说,“我们来比比,看谁先脱掉。”他开始解靴子上的绑带,伊尔德布兰达也接受了挑战。但这对她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紧身胸衣的架子让她弯不下腰。乌尔比诺医生故意放慢了速度,一直等到她从裙子下面掏出自己的两只靴子,就好像刚刚从池塘里钓上来似的。这时,两人看了一眼费尔明娜,只见在黄昏火红的霞光映衬下,她那黄鹂般的倩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轮廓清晰。“现在我发现了,”她说,“让我不舒服的不是鞋,而是这个钢丝鸟笼。”乌尔比诺医生会意她指的是裙撑,于是赶紧抓住了这个良机。“这再简单不过了,”他说,“脱了它。”说着,他以魔术师般的敏捷动作,从兜里掏出一条手帕,绑在自己的眼睛上。“我不看。”他说。
蒙在眼睛上的手帕一下子就让他那圆润下巴上的黑胡子和用胶刷出胡尖的短髭之间的两瓣嘴唇显得分外纯美。费尔明娜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可当她想把载着绸缎手套的手撤回来时,乌尔比诺医生却用力攥住了她的中指。“我在等您的回答。”他对她说。
除了对于乌尔比诺的私人好感,我可以很确切的表示,对阿里萨的厌恶与喜欢乌尔比诺没有丝毫关系,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还能这么反感一个书中之人的存在。对阿里萨的厌恶完全来源于我对于道德的评价,以及不赞同阿里萨逐渐‘堕落’而又逐渐适应这种‘堕落’的过程。阿里萨或许是书中19世纪里最缺爱的那个人,作文www.yuananren.com即使是被丘比特之箭射的千疮百孔的心,也丝毫没有停下为费尔明娜的跳动。阿里萨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意识到自己的爱再次来临了,而前不久他曾经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也有过同样的感悟。或许是最后看完这本书就像新生儿终于被剪断了脐带一样,我也放下了对阿里萨和费尔明娜在一起的反感,虽然不会兴高采烈的支持,但内心已经不会再被掀起万里巨浪了。
马尔克斯是伟大的作家,这一点从《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就能看出来,与这本相比,我显然更喜欢上一本。这种偏向是爱情的小说,如果不是里面有鲜活的、我喜欢的角色支撑着整本书,其实我很难深读此类型的书。不过到最后,无论如何,我还是当了一次马尔克斯手中绳索牵着的一条留着哈喇子的宠物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