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死亡,这是个问题。
《云中记》实体书籍的腰封上,明晃晃地摆着一行字“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安魂曲是罗马天主教会一种祈愿仪式使用的弥撒,具备特殊的规格、作品样式及丰厚意蕴,其本质与死亡相关,是面对死亡的沉吟与悼念。而《云中记》就像于《安魂曲》中窜跃而出的一个音符,单薄却又丰满,霎时起落却又余味绵远。
死亡是人类必得面对的生存逻辑中紧扣的一环,这一命题的演绎间不存有丝毫懈怠与迟缓,它偶有提前赴约,却从未缺席。云中村是汶川地震核心区的高山地区藏族村落,其生活方式及族人秉性都因信仰藏族的原生态宗教——苯教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神性。也因此,阿来的叙述之间便夹杂了浓厚的宗教气息。阿来的写作始于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十年,据他本人阐述,他具有这般创作冲动,却在等待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而这一时刻的到来,则足足有十年之久,十年后的地震纪念日,成都城内警笛声大作的瞬间,阿来热泪盈眶,他明白“开写的时刻,真正要到来了。”与长久等待后涌现的文字吐露一般,《云中记》的主人公阿巴,对于云中村的重归安魂之旅,他盘算好了日子,在距五年前地震发生前三天的5月9日离开移民村,回到云中村,这一过程也带有一定的“启示性”。与其说,阿巴重返云中村之旅是为了聊寄哀思与履行自己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祭师”的责任,不如说是他对于死亡记忆的重复书写与有关死亡意义的再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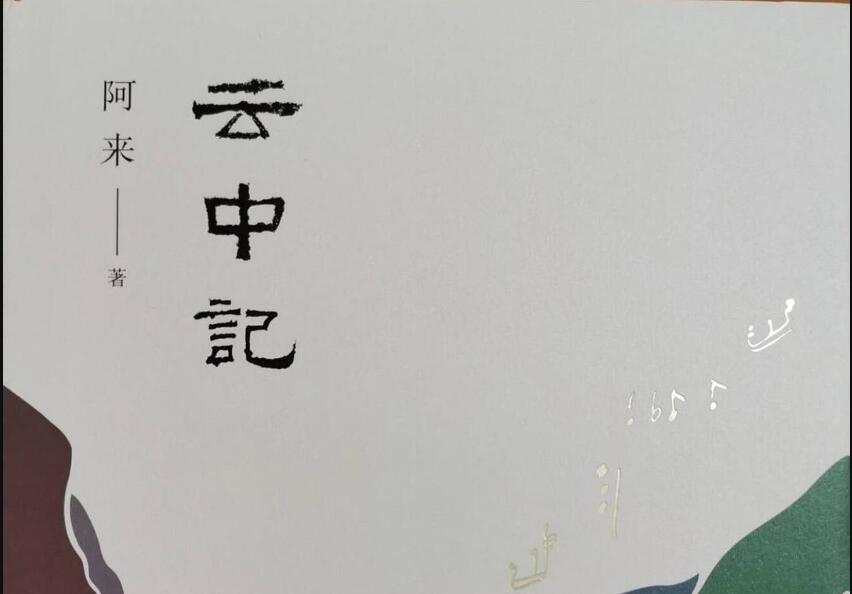
阿巴是《云中记》的主题脉络,细致场景的展开、细琐语言的呈现与质朴情感的涌现,都依托着他的框架向上攀附。阿巴是藏区本土宗教——苯教的祭师,同时也是政治文化意义认定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祭师身份赋予他的是对于神灵的信仰、对于生死之事的虔诚以及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内化到文本中,是阿来面对滑坡后垮塌的发电站,认为“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是阿来回村后以原始的自然生活的状态,与废墟之间万物的共处,代表全村人祭祀山神以抚慰亡魂,了却云中村人的心愿。这些举动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是人的原生心性与自然的崇高天性的相互渗透。可这也为阿巴带来了其躯体内部的隔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与自然的亲密性,也削减了他对于死亡那份来自自然的原生敬畏,因此他的返乡之旅,更大意义上是他的朝圣之旅,也是他逐渐走向死亡本质的赴死之途。
本雅明有过这般论述,经典的故事讲述围绕着死亡展开。而《云中记》中阿巴对死亡的觅寻和接纳,则是本书区别于传统灾难叙事文学的转折点。《云中记》中浓厚的宗教意味并未经由繁复的祭祀仪式等宗教活动加以阐明,它不动声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阿巴对自然与死亡的亲密接触之间。阿巴重返云中村后,云中村的景致向他呈现出的是没有人烟的村落、垮塌的房屋、纵生的野草以及角落天地里窜跃而出的几株油麦菜、麦子和玉米,这是自然与死亡的深切交融。作文www.yuananren.com受此景象触动,阿巴感慨道:“我喜欢云中村现在的样子,没有死亡,只有生长,什么东西都在生长。”垮塌的房屋是亡魂思念故人与今人想念逝者的思绪疯长,杂生的野草是死亡践踏过的大地上,生命与自然对死亡的抗衡与长久对抗。阿巴对死亡的接纳之中,也包含着对于生命的崇高信仰与敬畏。可仅有敬畏,并不足以实现阿巴对死亡的个人书写和意义界定,更为重要的是,《云中记》于个人意义上,将阿巴安息逝者亡魂的人性上升为以大爱促发死亡涌动为新生的神性,于群体意义上将灾难背后众人的伤痛记忆重塑为皈依新生生命之珍贵的虔诚信仰。《云中记》之所以可于“云中”叙事,并不仅仅在于它未曾将叙事重点放置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悲痛与无助之上,而是着眼于灾难过后人性的自我救赎与生命的新生。
阿巴在对于恒久长存的自然与倏忽消逝的短暂人世的辗转观望间,努力地贴近着世间万物,觅寻接纳死亡的途径,而最终浮现于他心头的那行文字便是——不仅要让生者接受逝者之离去,更要令亡魂于死亡之下得以享有安息。死亡是已然发生的、无可更改的事实。对生者而言,重兴对生活的信念,妥帖地重归生活轨迹,便已可尽生者之本份;对逝者亡魂而言,则唯有将其全数哀怨凄念平息,方可迎受新生。阿巴最终随云中村一并消失于深山云雾之间,看似是其皈依自身信仰、实现夙愿后的圆满与超脱,实则是其祭师自然本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这一世俗称号抗争之结果,是其自发人性与皈依之神性纠缠的产物,是自然与生命对死亡的超越与征服。如里尔克所言:“我们所谓的命运是从我们‘人’里出来,并不是从外边向着我们‘人’走进。”阿巴观照自身,于自己的“朝圣之路”上实现了对于死亡这一绝对事实的反叛与突围。
“再过些日子,罂粟花瓣就会干枯,就会被风吹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