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最终还是步入官场了,这是老师曾国藩的要求。他于同治八年五月抵达保定,再次入幕,十月,曾国藩外放他任磁州知州。
清朝的直隶省行政单元最为庞大,下属十府、六直隶州、四直隶厅、十七散州、一百二十三县。磁州(今河北磁县)是散州,属广平府,知州是从五品,级别高于知县(正七品)。清朝的州县岗位有“冲(交通枢纽)、烦(公务烦多)、疲(赋税拖欠多)、难(民风彪悍)”的分类,而磁州占了“冲、烦、难”三项,素称难治,按官场的说法是“要缺”或“繁缺”。但磁州比较殷富,又是直隶著名的“肥缺”。曾的用意很明确:一是培养人才,需要让烈文“下基层”磨练;二是从现实出发,做官可以挣钱养家。烈文还是像以往一样推辞,他不是虚伪——自己的性情历来畏难畏烦是原因,更怕干不好给曾国藩丢面子。
其实老师待他不薄——知州的级别虽不高,但有清一代,即便是科举正途的进士,三五年也未必能谋得像磁州这样的“要缺”,至于举人,五十岁以前基本没有可能。而烈文无疑走的是“军功保举”的捷径——谁都知道他和曾家的关系,苦等十几年还等不到实缺的那些后补官员们,不免眼红,烈文如履薄冰的心态亦可知焉。做官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主要是做人的尊严方面。以前烈文在曾幕,是客卿性质的下属,搁现代至少也是“首长秘书”,外出办事,即便巡抚一级的干部,见他也要客客气气的。那时候他写信,对李鸿章都是朋友式的口气,真从曾国藩算起来,李鸿章也不过是他的“师兄”。但进入官场,一切都不同了,等级森严,任命书一下,连对曾国藩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而以前懒得打交道的布政使、知府之类,如今都成了自己的上司,掌握着考核的权力,要轮到他毕恭毕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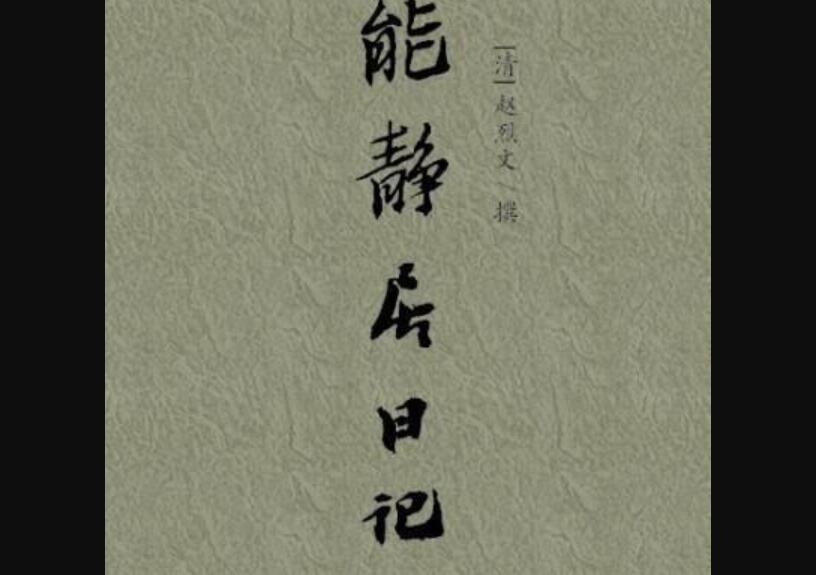
不过比起当官的实际好处,“清高”又显得多余,按道光年间洪亮吉的说法“守令之拙者,满任而归或罢任而返,其盈余虽不多,然恒足以温饱数世……今则十倍于前”(《卷施阁甲集》卷一),否则也不会那么多人眼红了。名义上,清代知州每年的薪俸是80两银子,这当然是开玩笑,还要有养廉银,而直隶省的州县官员,每年养廉银最高也不过1200两,还不够为幕僚支付报酬。一个州县官的正常支出,要包括摊捐、幕僚薪金、伙食费、接待费等好几项,每年约五千到一万两左右,而磁州是“冲”,直隶的南大门,迎来送往更要花钱,要靠巨大的“陋规”维持。“陋规”是一种官场潜规则,即地方各级官员可以自行收费以补充收入,法律是默许的,没有它,地方工作不能开展,因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必须的。但收多少陋规,完全凭官员的良知,所谓好官,就是陋规基本上用于公事,不用于自己致富,但这需要多高的觉悟!赵烈文固然是好官,后来调职,据说还留下州财政的亏空,可见其“刮民”不恶。但在那个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不爱钱,也不会受穷,此前日记中不见他任何消费的记录,担任州官后,购买精致版本的图书则屡见不鲜,可见其经济状况的改善。老师曾国藩诚然是严于自律的一代伟人,但出于亲密,还是为他“曲线”地解决了后半生的生活,他对此感激零涕。
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重任两江总督。南下时并不路过磁州,烈文特地赶到今天京冀交界的白沟河去迎接,陪了五天,一直送到河间才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曾国藩,临别“为之怆然”,而曾亦“闵默不复能谈”。这对师徒无疑是那个时代道德水准的标杆,但他们也无法摆脱文化惯性所编织的社会人情大网——在厌恶规则的同时,自己也不自觉地执行着规则,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继任直隶总督的是李鸿章,也是曾幕中的老关系,但十年间青云直上,官架子要大多了。李很看重烈文,对他早有“为何不投入我门下”的遗憾。然而在次年五月,烈文去职磁州,等候调职,本来稳拿的赵州知州缺,却被别人夺走。这是曾国藩离任的效应,李鸿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布政使等人早憋着换上自己人,烈文就这样吃了哑巴亏,暂时安排编撰《畿辅通志》。
转过新年,即同治十一年的正月,或许是直隶的长官们觉得对不住曾国藩的委托,或许是受到曾的直接压力,又委任烈文易州知州,仅赋闲半年即又履新职,后台还是很硬。易州不如磁州富裕,却是省的直隶州,下面还辖有涞源、涞水二县,属于“冲、烦”。知州的级别是正五品,庶几等于知府的从四品,烈文实际上是晋升了。作文www.yuananren.com而更有特殊意义的是,清西陵在易州,平时有宗室看守,搞不好皇帝也会来谒陵,知州的责任更大。但他上任才一个月,就传来了曾国藩逝世的消息,而此前他还为哥哥的工作麻烦老师,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此后三年,波澜不惊,只是在同治十三年二月,皇帝与两宫太后谒西陵,烈文记录详细,是很好的史料。但在接待的过程中,他得罪了监察工程的宗室,后者还去直隶告黑状,尽管李鸿章不以为然,但官场的黑暗让他心灰意冷,更何况对于一个预测政权五十年必亡的人,这个体制本身就不值得留恋。
光绪二年三月,赵烈文辞去易州知州职务,准备还乡。李鸿章不愿放他走,但他去意已定。他从未去过京师,绕路入都一游,南下途中,又游览了泰山、曲阜,于是,每天的日记都是一篇精彩的游记。其中关于北京旃檀寺的记录尤为珍贵,因为此地如今是国防部大院禁区,古迹已经没有了。他到家已是十月底,七年游宦,落叶归根,虽然才华未尽施展,毕竟官囊不薄,今后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了。
早在同治三年攻克天京之后,烈文就有求田问舍之志。他看中了常熟县城西南虞山脚下的一块地,开始建造私人园林,而北归之后,似乎更不愁资金,开始大力营造。如今常熟市区有“曾赵园”景点,是将曾朴(《晚清著名小说《孽海花》作者》的“曾园”与赵烈文的“赵园”合在一起,成为当地一大名胜。据说典雅清幽,媲美苏州园林,也算是赵烈文留下的“文化遗产”之一。
他的生活自此悠闲平静,爱好不过是收藏珍版书籍和金石碑帖,隔几年还会买个小妾。他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力依然偶露锋芒,如光绪二年上书李鸿章论外交,言“与其起衅而开边,毋宁口诛而笔伐。勿以强弱计成败,但取曲直论是非。得攻心之一言,胜浪战之万万……至于一日之计,则防清议重于防边;十年之安,则审敌人莫先审己。若进为长治久安之上策,盖不外用人行政之大端”,文辞足以媲美唐代陆贽的奏议!而这种清醒的见地,即使用于当世也不为过。
但他的身份彻底转变为乡绅,志向也转移到纵情山水,唯一让他有所顾虑的是子女的前途——毕竟维持这种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是家族最低的要求,为此,他不惜放下老脸,利用曾国荃、曾纪泽这些关系,为子女和亲属求职。此后的生活虽悠哉,亲友的相继去世却贯穿了整个隐退生涯,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在缓缓落幕。当他的日记戛然而止之时,自己的生命也似乎进入苟延,而即将进入二十世纪的满清王朝,也一步步地实现他的预言。
